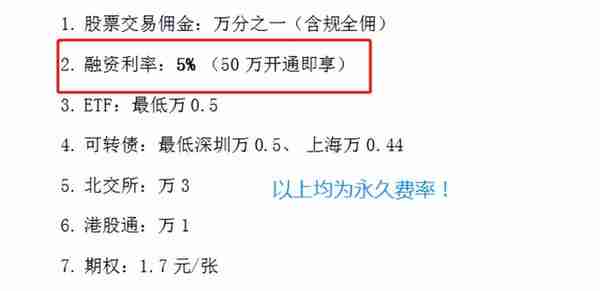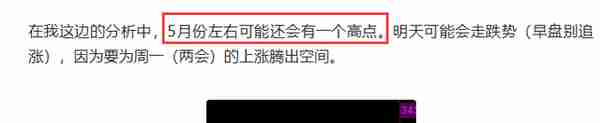罗鹿鸣《我想活得像一朵云》,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我想活得像一朵云》这本属于西部高原的诗集,是罗鹿鸣在青藏高原亲历与回忆交互作用的结晶体,也是一个摄影师对地球第三极人文地理经过心灵熔炼后的图像显影。作者运用摄影手法写诗,望远镜头、广角镜头、鱼眼镜头画面的自如切换、特写与蒙太奇的叠加,使诗作画意增强,境界拓宽,更加富有张力。一列列巨型山脉与一条条世界长河的经纬交织,结出了一颗颗动人心魄的诗茧。在这里,雪山化身为崇高,冰湖变体成圣洁,众生便是天地的王者。“我想活得像一朵云/这朵云,最好活在高原的蓝天/孤单、自由、而不失高洁/即使有一点放荡不羁/也是在天空的宽恕以内”。这挥洒自如的语调和一个个化茧成蝶的意象对应着作者的精神仪式和生命仪轨。借助物象和心象投射,来对高原回望、对人生回眸、对众生礼赞。这部诗集彰显出宽阔而深厚的质地,精神阶梯不断抬升的结果,便是神圣与高洁。
抬升的诗歌阶梯
——关于罗鹿鸣的“高原”诗系
文/霍俊明
我曾多次讲过诗歌既是自我发现又是心理补偿。诗人最先找到的往往是幽深的自我精神渊薮,而外界、环境以及物象往往都是心象的投射以及诗人情志一次次主动选择、过滤和转化的结果。从1984年开始的近四十年间,青海和西藏高原在罗鹿鸣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以及诗歌写作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称之为灵魂的坐标以及不断抬升的精神阶梯。
1
正如其最新的这本诗集《我想活得像一朵云》一样,西部的高原、高峰、天空成为罗鹿鸣不断抬升的眼光和不断拓展的襟怀,高迥之地就如不断抬升的大地阶梯一样它们对应于终极意义上的存在之真,对应于一次次的精神淬炼和洗礼。无疑,这是仰望、凝视、敬畏、辨认和自省、叹息、叩访、盘诘同步发生的过程,“天高、地迥,生出孤寂 / 生出我的一阵——冷颤”(《仰望星空,在珠峰》)。由此,诗歌也就成为了激发诗人求真意志和精神膂力的必要手段,一个个词语和意象也就自然对应了精神仪式和生命的仪轨。
对罗鹿鸣一直苦心孤诣地经营“高原”诗系的写作,我深有同感。他的青藏高原诗歌版图中的一部分我也非常熟悉,比如青海湖、格尔木、德令哈、西宁、巴音河、祁连山、拉萨、布达拉宫、林芝、尼洋河、雅鲁藏布江以及诸多高拔入云的雪山。对这些西部的空间和风物我感同身受亦心心念念。甚至在北京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那段时间,在封闭的斗室内我在一个又一个夜晚观看关于西藏、青海和新疆的人文纪录片,在那些雪山、戈壁、大河、星空、寺庙、历史废墟以及芸芸众生的面孔中我获得了重新面对时间与审视自我的机会。
熟悉罗鹿鸣的朋友们都知道,除了作金融工作之外,他还有着诗人、驴友以及摄影发烧友的多种身份,甚至这么多年他所拍下的照片数量要远远高于他的诗作,“万籁俱寂之际,快门 / 十分刻意地咔嚓一声 / 凄美的星轨,带着 / 连绵的忧伤,蜂拥而入 / 相机,宅心仁厚”(《仰望星空,在古格王朝遗址》)。诗歌和摄影成为罗鹿鸣观看世界的两个取景框,它们具有内在的差异又相互补充,诗人的眼界、经验的边界、认知的边界以及语言的边界不断得以扩展,“鱼眼镜头看星空 / 比我看的宽,比我看的远 / 甚至可以看到身后的一部分事物 / 背后的东西往往很黑暗”(《仰望星空,在墨脱》)。
对于罗鹿鸣的诗歌和摄影而言,差异性的视角带来了更多的情志空间和多层次的真实度。当一个诗人举着相机站在浩瀚的星空和冷峻的雪山之下,加速度旋转的精神视界近乎是梵高般的燃烧。摄影是生活经验的呈现,往往由主体和背景两部分组成,在特殊的空间和时间节点上摄影还必然承担着个体主体性的认知、判断和精神姿态。在镜头的拉伸、移动、放大或者背景虚化的过程中真切的绒毛般的质感被放大和强化为感官化体验。这一切如此真实但又经过了精心的摆放、筛选甚至过滤和变形。
2
诗歌往往以个人为中心、原点和半径,进而追踪和认识物性或精神性的瞬间,这体现在写作中往往落实为物象、情绪、经验、意识和心智的可见性、可感性。再进一步的话,具有重要性的诗人则在精神穿透力中观照不可见之物和不可感之物,习焉不察的物性和日常情境也因为发生转义、变形,物象成为深度意象和象征体系。这类似于当年里尔克所提出的球形经验。但是,世界的完整性和凝恒状态已然消失了,固态的封闭社会被液态的流动碎片所取代。土地伦理和大体共同体也随之解体了,时间、空间、景观、心态都断裂了。在一个骤变遽然的全球化时代,从我们内心取走的东西越来越多,诗人的凝视状态也宣告结束了。为此,西部的高原以及耸立的雪山仍然代表了人类恒常如新的伟大精神元素,它们也必然吸引诗人、摄影师、地理学者以及转山者们极其专注而又不断抬升的目光。
值得一提的是,罗鹿鸣“高原”诗系的写作并不同于泛泛的“观光诗”“旅游诗”和“地理手册诗”,尽管其中一部分诗确实来自于常年的游历,但是这些“高原”诗歌所产生的心理机制和情感动因与观光客浮光掠影式的观看和体验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西部和高原对于罗鹿鸣而言不是外在的,而是有着切实的工作经历和生存感受,甚至他还有亲身攀爬珠峰大本营的经历。譬如罗鹿鸣对尼洋河的认知就是通过灾难性的三次车祸来完成的。
这些高峰、星空以及雪水、戈壁逐渐成为不断与诗人进行对话的终极命运伙伴,它们所携带的巨大的心理能量也一次次将尘世中浸淫日久的困顿、疲惫、焦虑的灵魂重新激活、洗刷,“星空又历历在目 / 它的演出一直在按部就班进行 / 我呢?早已不在原地 / 早已告别了幼稚与童真 // 一颗流星划过天际 / 那是我情不自禁 / 仓皇出逃的 / 一滴清泪 // 幸好,有雅鲁藏布江接着 / 才在破碎之后,尚余 / 涛的回声”(《仰望星空,在墨脱》)。
3
让我们拨转时光的指针,逆着影像的胶片回到1984年。
罗鹿鸣与那一时期的年轻人一样都无限痴迷于“远方”和“在路上”的状态。大学毕业时他主动申请到青海支边。在德令哈的茫茫大戈壁上,一个年轻人在大风中的身影被诗句所击中,一颗坚定而热烈的心也因此得到了诗神的眷顾。当时,罗鹿鸣是德令哈二中的教师。在罗鹿鸣八九十年代的诗歌“高原”“土伯特人”“牧人”“盆地”“戈壁”“莽原”“海子”频频现身,青春、热望、爱情和梦想都在剧烈地燃烧,它们也照彻了一个青年诗人激越而焦灼的脸庞。这一西部工作经历和生活经验构成了罗鹿鸣诗歌写作中的“纪事”系列,即最新这本诗集《我想活得像一朵云》中的第二辑“青海往事”。
罗鹿鸣早期的诗带有八十年代以来“文化史诗”的一些影子,这些磅礴、鼓荡、激越、惊颤、跳动、炸裂而犹如彗星般急剧加速燃烧的话语方式正好是对那一时期“青春期写作”的呼应或告别,“他们用糌粑用手抓用奶茶雕塑骨架 / 站立如大山躺倒如巨原奔驰如羽翼之马 / 他们将哈达从历史之死线团里拽出来 / 拽出来成白洁之河流过生与死 / 涨起诞、婚、节日之方舟”(《土伯特人》)。
随着人生阅历、写作经验的丰富,高原作为终极信仰也一次次淬炼着诗人,值得注意的是罗鹿鸣不同时期的高原抒写有明显的区别。
罗鹿鸣诗歌中的语调、表情以及精神氛围总是让我想到一个凝恒、精敏的凝视者,一个不断抬高精神视线的仰望者,一个不断摩擦、盘诘的内视冥想者。这些雪域高原以及连绵起伏的群山在罗鹿鸣这里既是物理性的又是精神性的、时间性的,既是此岸的又是彼岸的,既是可知的又是不可知的。
罗鹿鸣往往是站在历史时间、自然时间、地方时间以及精神时间的交叉点上,这既是历史法则又是人的价值尺度。所以在诗人的综合视野中,一座高山、一架冰川、一颗流星、一条大河、一朵流云、一堆玛尼石、一个村庄、一只渡鸦、一座雕像、一粒青稞、一头盘羊、一个野牦牛头骨往往能够被最大化地激活,其间渗透着诗人的情感、经验、认知、知识、智性以及想象力,当然还有令人震惊、敬畏的大自然恒常不变的伟力和膂力。
森林如戟,张扬着白云的旗袍
雪峰戴着刺眼的头盔,冷漠相对
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举着一双巨鳌
像夹着一粒沙子,丢我于咆哮之中
河面上白雾宛如展开的绢布
将我们的行迹裹挟,捉摸不定
——《山桃花开》
这对应的既是个体时间和精神时间又是总体性的世界时间以及地方时间,对应于世相人心和时序流转。
4
一座座雪山以及苍茫的戈壁既是自然背景,也是高原世界作为精神元素的化身,它们构成了一个诗人的信仰和命运的根底。这些终极元素的化身对应于历史和现实,对应于物象、心象和幻象,对应于一个具体存在者的感受力和想象力。由此,个人情势与精神元素在西部高原完成一次次的对视、叩访与盘诘,诗人的生命意志也因此得以不断地磨砺、调校和修正。
高原与大地一样都是一个有机体,所以写作者必须把它们提升到生命乃至灵魂的高度,“里面的组成部分和人体组织很相似,每个部分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是有机体内运行的一部分。你只能小心翼翼地调节各个部分,却不能去掉某个部分。”(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由此衍生出来的是“高原伦理”代表了稳定、完整、原生、固态的精神结构。罗鹿鸣的高原写作印证了“高山”与“天空”是彼此映照的垂直共同体,失去了任何一方都会导致世界秩序和精神世界的土崩瓦解,“盲女在里尔克的诗里哀叹:‘我再不能与头上的天空共存。’我们该对她说什么呢?若说我们再不能与脚下的大地共存,可会令她稍感安慰?”(E.M.齐奥朗《眼泪与圣徒》)
罗鹿鸣这些“高原”诗系的意象具备典型意义上的“西部”特征。如果诗人对这些意象的构成以及历史没有深入地了解,如果没有独特体验对“词与物”考古学意义上的重新校正和激活,那么这些意象体系很容易成为空洞无物的符号。罗鹿鸣这些“高原”诗因为写于不同的时间段,所以文本面貌也自然不同。越是到了晚近阶段,这些诗就更为自然、完整,更具有对话的结构和精神启示的效果。其诗歌中的自然风物以及物态的日常功能已经提升和转化为不断辐射、无限敞开的精神能动空间和情志动态结构。也就是说,自从有了人的观照、体验、感悟、记忆和主观能动性的参与之后,任何一个空间、物象就不再是纯粹物性的了,而是心智过滤之后的精神产物。这些物象、细节以及场景在生命意志的一次次擦拭和深度参与中成为了精神共时体,它们一次次激活了诗人内心的生命源头,也改变了诗人与自我以及整个世界的惯性认知关系和条件反射。
这些诗对应于内心的潮汐和精神的元宇宙,在一座座高山大川面前任何一个人都会成为一样仰望者、赞美者和鼓胀的“抒情诗人”和“地方主义者”,所以在罗鹿鸣的诗歌中我们既听到了法号声中的唱颂又听到了低缓的陈述与自语。这些高低起伏的声调对应于具体时刻或抽象境遇中一个人内心的所思,对应于对自我、时间、生命的反省。
5
任何一个人面对着雪域高原或茫茫戈壁写诗,光凭暂时性的陌生感、新奇体验以及表皮式的抒情诗是得不偿失的,他一定要具有澄怀观道的能力,具有内视的反思精神,具备对高大之物以及幽微之物长时间的凝视的耐心,具有深度叩访的精神求真的意志力。
在诗人这里,万事万物都是等量齐观的,高大之物的几何图线与细小之物的幽微纹理都具有同等重要的精神启示效果,“脚下五十多公里的转山道 / 磨炼了无数的世事人心”(《冈仁波齐的笑脸》)。这时候诗人就不知不觉地成了精神修习者。物象、意象、心象和幻象在终极元素的背景下构成的正是一座座坛城。
坛城,是视觉化的佛之城——轮圆具足,是“获得本质”的法门,也是心力、心象和世界、因缘场域相遇和交互的过程。人格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就绘制过多幅曼陀罗,最早的一幅绘制于1916年,有些曼陀罗的图案和结构则来自于他梦中的启示,“由此形成情意丛的原型表现一种秩序模式,这种秩序模式作为心理十字线或作为四等分圆周某种程度上被置于心理混乱之上,由此,每项内容各得其所,四散不定的整体由防患于未然的圆周加以集聚。”(荣格《现代神话——论天空中所见事物》)2015年夏天,我在布达拉宫第一次与坛城相遇,这一“心中宇宙图”、“四曼为相”是如此微缩、具象而又如此直抵世界的本体和终极核心,“两名西藏喇嘛手握铜质漏斗,俯身朝向一张桌子。彩色的沙子从漏斗顶端泻出,洒落在桌子上。每天细流都为逐渐扩大的坛城增绘了一根线条。喇嘛们从环形模型的中心开始,先沿着粉笔标出的印记描绘出基础轮廓,而后依靠记忆,对成百上千处细节进行填充。”(戴维·乔治·哈斯凯尔《看不见的森林》)在罗鹿鸣这里,记忆之物、自然之物、宏阔之物以及卑微之物已形成三千大千世界,甚至它们就是坛城本身,是世界的本质象征。诗人的“坛城”是维系自我、人格以及生命、记忆完整度的特殊途径和观照方式。在罗鹿鸣这里,开阔的胸襟、优异的视力以及凝视的状态都是为了保存世界的本相,都是为了保持对一个个日常化的细节和空间进行精神层面的现象还原。
永恒与短暂,仰望与自省,已知和未知,自我和世界,“词与物”,它们时时交错、共振、对谈、盘诘。此时,诗歌就必然起到维护生存作为一种记忆方式的终极功能。在生命意志和个人化的地理想象力的深度参与下元素之诗、地方之诗以及生命之诗都得以复活并寻求永生。这也使得诗人不再是一次性肉身的短暂废墟以及爱恨贪嗔痴的虚妄载体,而是词语和意志垒砌而成的白塔以及从雪山之巅奔流而下的澄澈的灵魂。
最后,还是让我们一起听听诗人的自渡之歌吧!
山是神山,水是
圣水,人是
生生不息的
活菩萨。生
是死的现在词
死,是生的未来式
——《雪域书》
附:罗鹿鸣诗集《我想活得像一朵云》作品选
购书可联系罗鹿鸣微信:LLM298886609
◎我想活得像一朵云
我想活得像一朵云
这朵云,最好活在高原的蓝天
孤单,自由,而不失高洁
即使有一点放荡不羁
也是在天空的宽恕以内
没有强大的云海,作为组织
更不要厚重的云层,当作后台
向往一种简单的幸福
使姿态也变得简简单单
不管群山是否仰望
不管江河如何评判
不管方向是否分为西北东南
那怕就要消散于无形
也保持一种对天空的忠贞
◎仰望星空,在纳木措
在神山圣湖的中间
站着我,在雪与水的
上方,站着神
此夜,我与星星
互相凝望,辨认对方的
胎记与手印
住在上天的神灵
它们,一直俯视着
大地与众生
念青唐古拉,冰肌玉骨的
主峰,闪射着冰雪聪明
那一缕白云,在
阳光里曾经来过
它的前世,来自
高迥,我曾与它们
在天庭对饮
我诀别内地才恍然大悟
原来星光是如此醍醐灌顶
瞬间即逝的星光
还不如一丛麦芒来的实在
但它,却在高远的地方
刺醒心灵,予以
拯救
一脉雪山,是前世的宁静
一湖圣水,是今世的动荡不安
一群星光,是来世的幸福
全部汇入我的瞳仁
此时此地,我的内心
充满澎湃的光明
亦如启明星
燃烧的
静
◎我的青藏高原
雪线之上,是凛然的尊严
神在山顶相聚,抱着白云狂欢
天空是他们可以依赖的亲人
星星是他们一起玩耍的伙伴
日月交替,为他们掌灯
他们将真理垄断在远离人烟
雪线之下,岩屑流成石瀑
一种很抓狂、迷乱的力量向山脚蔓延
面对这乱石奔流的破碎山体
谁来为这个局面埋单?是高处
焦虑的失语,是内心膨胀的破裂
是一切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奈与无助
幸运的是:雪山破碎,而人间静好
干打垒矮屋、黑牦牛帐房袅娜着炊烟
黑框白墙的窗棂飘溢出奶茶的香甜
在高原上袅窕着升起的柏油公路
很有礼貌地造访摩托车出没的藏寨
卡车像一个甲壳虫从远方爬过来
在眼前又变成一头风驰电掣的野马
转眼间缩做山路上一张蠕动的叶片
那一条条自雪山肚腩流出的冰河
时而狂躁如斗兽,时而乖巧如悬鸟
一座一座的桥梁为其戴上手镯
羊皮筏子靠在墙角过起退休生活
马车的叮当声,没有听众也在悠扬唱歌
远眺的姐姐,自在地倚在门前
目送着弟弟的黄袈裟与白云为伍
寺庙是从毁圯的寺庙上长出来的
不太巍峨,不太绚丽,但足够
那些磕着长头过来的灵魂安居
胡杨在大殿的两侧,像忠于职守的
卫士,在昏黄的、明灭的稣油灯
照不到的高度,头发由青变白
我不断地接近那座神秘的天穹
接近那座高出人间无数的圣洁峰峦
像约会初恋的情人,满怀波澜
我眺望着一列列雄壮的山脉
它们披着云的霓裳,甚至用霞光
捂住威严的额头,透出高不可攀
当我走过九九八十一条道路
当我经历九九八十一次磨难
我终于揽住了你的坚硬的裙裾
我站立着行走,我无法跪下双膝
你是我的亲人,是我离散已久的亲人
一双泪眼为我们的重逢汩汩涌泉
亲人啊,你又为何高高在上
舍不得递给我一张擦泪的纸巾
我的泪水,涌成满天的星辰
随着长曳天庭的星河滔滔而去
亲人啊,你又为何掩盖着真容
让我执手,却又遮盖令人仰望的皱纹
难道你早就洞明了世事沧桑
而我无法做到人情练达、世故圆滑
惭愧的雨水冰凉冰凉,打湿脚下的砂砾
而且,我看不到你的侧面与身后
不知道那里藏匿了多少天机与宝贝
一个在转山的路上葡进花甲之年的人
再也不奢求金银珠宝,我会像掏出
珍藏已久的宝贝那样,向你掏出自身
◎土伯特人
高原如盾牌抵挡太阳之箭抵挡雪风之九节鞭
岁月之利戟还是把它砍伤了沟沟壑壑可供考证
这自然之杀戮却催生了一群高原之子
他们同牛毛帐房一道菌开在漠野
他们是土伯特人是高原青铜之群雕
他们用糌粑用手抓用奶茶雕塑骨架
站立如大山躺倒如巨原奔驰如羽翼之马
他们将哈达从历史之死线团里拽出来
拽出来成白洁之河流过生与死
涨起诞、婚、节日之方舟
他们用锦袍用狐皮暖帽用牛皮靴子
给生活刻划线条给牧歌插上翅膀给人生打上戳印
从莽原索取野性冶炼成粗犷锻压成豪放
却将绵羊牦牛驯化成温顺之楷模给女人效尤
却不把奔马之四蹄驯化成没有脾气的木头
否则就没有女人用丛生之发辫去缠他们的肩膀
女人们古今都是天地牙缝中的尤物
金戒指银耳环白项链绿玛瑙把每一个晨昏碰出声音
她们以此为马尔顿来打扮穷富
笑花和泪雨和情人的眼睛也少不了它们装饰
就这样一丛华贵的金属给她们套上了重轭
经过少女嫁娘老妇之驿站没能松脱始终
他们用火抹去生老病死之苦痛
他们请鹰隼腹葬总难结果之欲望
让灵魂在活佛念珠的轮转中超度永远
然后把天堂在心上筑成浮图
他们幸福的归宿便在脸上开出高原红
他们古朴善良独角兽一般纯洁
他们是土伯特人是高原青铜之群雕
◎永远的橡皮筏
——献给长江首漂勇士尧茂书
于是,我戴着雪峰之头盔行进没有回头
行进在雪莲、红柳、沙枣花的队列
行进在历史与现实交响的休止
两岸之沙丘像我的痛苦无目的地搬迁
白毛风是我的歌子传播我的悲喜
我抖动肩膀将星星的注目搅得模糊
我合张的肺叶如江河源奔泻迂回
给我橡皮筏给我意志之木桨吧
我要漂流流出历史之河床流向立交构思
让野驴、野牦牛列成游动之堠堡迎接
让白唇鹿因嫉妒而奋蹄叩击回浪之悬崖
让天葬之悲声将我推向波动的原平线
让欸乃之声让涌浪之声覆盖我的灵魂
让生死之狭缝里突发最后一道闪电
抽落我三十年里森林般的日子
不知道世界多大而自己只是地球上的流萤
应该通体燃烧照亮哪怕簸箕大的一块沉静
长寿的碌碌无为不见得胜过辉煌的短暂
如此我在千万人目光的摸触中沉船
波浪笑得平静我拒绝不了它的诱惑
然后变成鱼在长江下游听渔歌号子
变成记忆在后生中听怯弱的忏悔
变成灵感迫使小说家的笔戳穿稿纸
使自然对我刮目使所有的不解者对我仰头
我沉生为暗礁这是水族为我立的丰碑
我将更多膜拜我的化身召集起来编成连排
在某个咯血的早晨突然长大为一座山
使河流改道听任吩咐我是自然之王子
令滂沱的天文雨抹去缺乏钢性的花
令殒落的警钟在历史的长廊里震响不息
人们意识了昔日之可悲胆子赶不上漂流之枯叶
便有蝗虫般涌来的橡皮筏向未来宣示什么
◎青海湖诗歌节诗墙
石头,不一定
永远是一块石头
石头的眉额刻上诗歌
石头就能飞翔,就能唱歌
从此,石头新生
诗歌不朽
湖畔的玛尼堆不说藏语
它的发言权委托给了波涛
天空肆意地生长梦想
诗歌啊,睡在青海湖床上
平展如镜的眠床
有时波摇浪晃
睡不踏实的诗歌
按捺不住歌唱

霍俊明,1975年生于河北丰润,诗人、批评家、文学博士后,《诗刊》社副主编、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喝粥的隐士》《怀雪》等诗集、散文集、随笔集等专著十余部。曾获首届扬子江诗学奖、《人民文学》年度批评家表现奖、《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诗选刊》年度评论家、《星星》诗刊最佳评论家奖、《草堂》年度诗歌批评家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首届全国海子青年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等。

罗鹿鸣,诗人、作家、摄影家,现居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常德市诗歌协会、湖南省金融作家协会、湖南省诗歌学会创始人。现供职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兼任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昌理工学院特聘教授。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内外报刊发表诗歌1000多首,作品被《新华文摘》《读者》《中外文摘》等报刊转载;出版诗集与报告文学共15部,主编诗歌、金融为主的图书80余部(卷),获第八届丁玲文学奖一等奖、中国金融文学奖一等奖、中国桃花源风光摄影大赛金奖等奖项。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