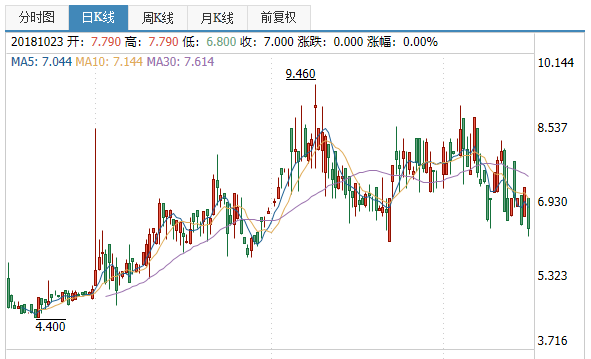结语 风险投资,国家力量经久不衰的支柱
对任何创作过电影、图书、播客或歌曲的人来说,纪录片《寻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一定让他们难以忘怀。这是一部关于底特律天才歌手兼词曲作者西斯托·罗德里格斯(Sixto Rodriguez)的影片,人们经常将罗德里格斯与鲍勃·迪伦和凯特·斯蒂文斯进行比较。20世纪70年代初,年轻的罗德里格斯发行了两张专辑,但都没有激起任何水花,唱片销量惨淡。于是唱片公司抛弃了他。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当一名拆迁工人,进行破坏而不是创造。在接下来的30年里,罗德里格斯在一栋废弃的房子里渐渐步入垂暮之年,这栋房子是他在政府拍卖会上花50美元买下的。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有些了不得的事情发生了,澳大利亚人和南非人发现了罗德里格斯的专辑并为之着迷。一家澳大利亚唱片公司将他的歌曲制成合辑,他的唱片的盗版版本在南非销售超过100万张,达到了白金级销量。他的一首歌成了反种族隔离的圣歌,但罗德里格斯本身对自己的明星身份一无所知。当我第一次通过纪录片看这位歌手在声名大噪的同时又默默无闻地生活时,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南非的一位朋友,问他是否听说过罗德里格斯。他回答说当然。他知道每一首歌曲的全部歌词,那些歌曲是他成长过程中的背景音乐。
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有一位名叫马修·萨尔加尼克(Matthew Salganik)的博士生作为社会学家更仔细地研究了“小糖人现象”。毕竟,与罗德里格斯的故事相类似的各种版本在创意领域一再出现。例如“哈利·波特”系列作品,尽管最初被出版商拒绝,但它最终轰动一时。许多图书、歌曲和电影都足以让人成名,然而大部分的战利品还是被少数人收入囊中,萨尔加尼克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偏斜的结果。因此,他与一些合作者一起设计了一个实验,他的研究结果为我们评判风险投资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萨尔加尼克创建了一个网站,人们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听不知名艺术家的歌曲,然后选择将其中一些歌曲下载到自己的曲库。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虚拟房间,这些房间完全处在“平行世界”,就如同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南非那样互不相干。不出所料,参与者更有可能选择其所在房间内的其他人已经下载过的歌曲,这意味着他们会对社会影响做出反应。随着最初的人气作品获得的关注如滚雪球般增长,每个虚拟世界都创造出了自己的超级热门歌曲,那首歌比其他歌曲更受欢迎,它的胜利看起来是必然的。但这种自然产生的优越的表象是有误导性的,在萨尔加尼克创造的实验世界里,不同的歌曲脱颖而出。例如,一首名为《禁闭》(Lockdown)的歌曲在一个世界排名第一,但在另一个世界的48首歌曲中排名第40,尽管两个世界中的歌单完全一致。萨尔加尼克总结说,引起轰动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随机产生的。
当然,这个结论鼓励明星风险投资人们谦逊处事。由于呈指数级增长的企业产生的反馈效应,一些风险投资人成为行业中的主导,可以筹集最大份额的资金,也最容易获得最热门交易,并产生最佳业绩。但与此同时,行业中的其他基金将举步维艰:如果统计1979年至2018年期间进行过募资的风险投资基金,我们会发现中位数基金的表现略逊于股市指数,而前5%基金的表现则远超股市指数。但是,至少从理论上讲,这场竞赛的赢家可能只是运气好,最初的成功会让网络的飞轮效应运转起来,可获得这场成功可能只是随机事件。如果我们能模仿萨尔加尼克的实验,让历史重来几次,也许“哈利·波特”系列作品的某些版本会默默无闻,也许凯鹏华盈会投资Facebook而不是交友网络,也许高盛集团的老板会继续持有阿里巴巴的股份,从而剥夺孙正义第二次复出的跳板。在历史的任何版本中,指数法则都会确保少数赢家成为超级明星,但谁是明星也受运气因素的影响。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直接在风险投资行业验证了这一逻辑,果然,作者证实了反馈效应的存在。报告中称,风险投资公司的早期成功会提高其后续成功的概率:风险投资公司的前10笔投资中每增加一笔IPO,预示其后续投资的IPO率将提高1.6%。在测试了各种假设后,作者得出结论:由于反馈效应,初始的成功会为后来的成功奠定基础。根据作者的说法,由于最初一两次的成功,风险投资公司的品牌会变得足够强大,能够赢得有吸引力的交易,特别是后期阶段的交易,那个阶段的初创企业已经表现良好,投资风险较小。此外,最初的一两次成功似乎并不能反映风险投资人的技能水平,相反,成功来自“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换句话说,来自好运。就像萨尔加尼克用歌曲做的实验一样,运气和路径依赖似乎可以解释谁会在风险投资行业的竞争中获胜。
风险投资人的贡献不容低估
不同于以上观点,本书驳斥了随机性理论,强调风险投资技能的重要性,这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原因。第一,路径依赖的存在并不能证明风险投资技能是不存在的,风险投资人需要运用技能才能参与其中:正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路径依赖只能影响众多技巧娴熟的参与者中何人会成为赢家。显然,路径依赖关系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熟练的经营者会赢过其他人。所投标的成功上市发行的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组合成员的未来IPO率会提高1.6%,这一结果不够有力,而且本书所叙述的历史表明,路径依赖经常被打破。尽管阿瑟·洛克有着强大的声誉,但在投资苹果公司后,他的成功事迹大大减少。梅菲尔德风险投资公司是20世纪80年代的领头羊,但后来它也销声匿迹了。凯鹏华盈证明,即使一家企业已经主宰了硅谷25年,它的经营状况还是可能急转直下。阿克塞尔在早期取得了成功,但后来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然后才重新站稳脚跟。为了让自己保持多疑和警惕,红杉资本曾在一张幻灯片上列出了许多后来被他们称作“往生者”的风险投资合伙企业,这些企业都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繁荣后失败了。
体现风险投资技能重要性的第二个方面在于一些风险投资合伙企业的起源。偶尔会有进入风险投资精英圈的新人证明技能显然很重要。凯鹏华盈成为行业的领导者是因为天腾电脑和基因泰克,这两家公司都是在凯鹏华盈内部孵化出来的,并由汤姆·珀金斯积极塑造成型,这与运气完全无关。老虎环球基金和尤里·米尔纳发明了后期风险投资的艺术,他们拥有一种真正新颖的科技投资方式,这种方式所带来的竞争远不止是像一首歌曲争取流行传唱一样简单。保罗·格雷厄姆在YC创造了新颖的种子期投资方法——批量投资方法。这一巧妙的创新,并非偶然的运气,它解释了为何格雷厄姆在风险投资史上拥有如此地位。
第三,认为风险投资人是借助其品牌优势而得以参与交易的观点可能被夸大了。红杉资本合伙人发现的交易也会被其他公司的竞争对手发现:在一个充满像家庭作坊一样的公司并且分散程度很高的行业中,并不缺乏竞争。通常情况下,赢得一笔交易不仅取决于风险投资公司的品牌,也取决于风险投资人所拥有的技能。这些技能可以帮助风险投资人充分理解目标企业的商业模式,从而在交涉过程中打动创始人,也可以帮助其判断什么样的估值才是合理的。一项严谨的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在最热门的交易中,新加入的或新兴的风险投资合伙企业获得了顶级交易中大约一半的收益,而且有无数的例子表明,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会搞砸投资机会。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错失了优步的投资机会,其品牌效应并不能挽回它。彼得·蒂尔是条纹支付的早期投资人,但他缺乏像红杉资本那样大量投资的信心。至于大品牌的风险投资合伙企业是否有参与本应风险较小的后期投资轮的“特权”,每笔交易的情况都各有不同。独角兽公司的势头通常会转化为对其股票的极高估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投资的风险。在优步和WeWork的案例中,一些后期投资人因此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第四,否定风险投资技能重要性的观点低估了风险投资人对被投公司的贡献。诚然,这些贡献可能很难界定。从担任了英特尔董事会主席33年的阿瑟·洛克开始,大多数风险投资人都避开了聚光灯,他们担任的是类似教练的职务,而不是运动员。但本书挖掘的多个案例证明,风险投资人的指导对初创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唐·瓦伦丁将雅达利和思科从混乱中解救出来,恩颐投资的彼得·巴里斯预见了悠游网络能将通用电气信息服务部门的技术网络化的未来前景,约翰·杜尔说服谷歌员工与埃里克·施密特合作,本·霍洛维茨引导尼基拉公司和奥克塔公司度过了其成长阶段。可以肯定的是,风险投资人指导被投公司的故事可能夸大了风险投资人指导的重要性:至少在这些案例的一部分中,创始人可能可以在没有投资人建议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定量研究表明,风险投资人的指导确实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多项研究发现,由高水平的风险投资人支持的初创企业比其他初创企业更有可能成功。这些文献中有一篇奇妙的文章,探讨了当飞机航线让风险投资人更容易访问一家初创企业时会发生什么。结果显示,当旅程变得更简单时,初创企业的表现会更好。
正如西斯托·罗德里格斯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早期的运气和路径依赖在依照指数法则运行的行业中发挥着作用。当然,风险投资也不例外,有时运气比智力更重要,想想安东尼·蒙塔古,这位挥舞着牙刷的英国人抢到了一块“苹果”。但聪明才智仍然是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就像风险投资人在工作中所展现的其他品质一样:首先,风险投资人要努力地和冷淡的创始人建立联系。其次,风险投资人要拥有一颗坚韧的内心,才能让自己安然度过投入变成零时不可避免的黑暗时期。最后,风险投资人要依赖高情商去鼓励和指导有才能但不守规矩的创始人。伟大的风险投资人可以把自己变成调节创业者情绪波动的“工具”。当被投公司进展顺利时,他们会问创业者一些探索性的问题,以免其滋生自满情绪;当情况不妙时,他们会团结整个团队,重新点燃团队成员对达成使命的热情。
风险投资是推动进步的力量,而非引发倒退的元凶
本书还提出了第二个论点。无论某个特定的风险投资合伙企业或单个风险投资人所掌握的技能如何,风险投资人作为一个群体对经济和社会都有积极影响。例如,苹果的融资显然不是证明风险投资人技能的典型案例。尽管独立个人电脑制造商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却仍有几位风险投资人犯了错误拒绝投资,但不管单个风险投资人犯了什么错误,风险投资人群体最终还是资助了史蒂夫·乔布斯。结果这家公司取悦了无数消费者,为员工创造了就业机会,也为投资人创造了财富。
正如本书对风险投资人个人技能的看法一样,社会对于风险投资人群体的质疑也有正当的理由。这些质疑可以分为三类:第一,风险投资行业更擅长填满自己的腰包,而不是发展对社会有用的企业。第二,风险投资行业由少数白人男性主导。第三,风险投资行业鼓励失控的颠覆者,而不考虑那些被颠覆的人。
这些质疑中最没有说服力的是风险投资行业支持的企业对社会没有用处。诚然,大型科技公司也有阴暗面。像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这样的大公司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影响,有些是好的影响,有些则不是,而政府取缔公司恶劣行为的做法是正确的。对隐私的侵犯、假新闻的传播,以及私营企业在信息传播方面的绝对权力,这些都是监管机构的合法目标。但这不该是对风险投资行业的控诉。当风险投资公司最初支持科技巨头时,他们是在帮助其创造对消费者有益的产品。现如今,没有人愿意再回到一个没有电子商务、个人电脑、社交媒体或网络搜索的世界。如果说这些科技巨头后来变得具有威胁性,那是因为它们已经变得太过庞大:在它们的发展轨迹中,风险投资的影响或者公司在初创阶段的初心已经被远远抛在脑后了。我们也不能说,风险投资公司在这些公司还处于摇篮中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把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灌输给了它们。事实恰恰相反: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倾向于让创业者更谨慎地对待法律和社会约束,而不是毫不关心。在Facebook,阿克塞尔在肖恩·帕克破坏公司文化之前就将他驱逐了出去。在优步,基准资本最终将卡兰尼克扫地出门。与此同时,风险投资人已经投资了几十种明显有益处的技术,例如数字地图、在线教育、生物技术等。风险投资公司投资建立的公司更多的是推动进步的力量,而不是倒退的源泉。
风险投资公司也因其未能建立的公司业务而受到攻击,因为他们犯了遗漏的错误。这种攻击最常见的理由是,风险资本更多流向了琐碎的应用程序,而不是对社会有用的项目,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领域。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并不是因为风险投资公司对这些领域缺乏热情。2006年至2008年,风险投资人向风能、太阳能电池板和生物燃料领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使流向清洁技术的资金数额增加了两倍。这些绿色风险投资基金的糟糕表现凸显了风险投资人对环境保护的热情:可以说,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使命感置于对有限合伙人的责任之上,而这些有限合伙人中有很多是大学和慈善机构。此外,自2018年以来,风险投资人再次展示了他们对清洁技术的热情,他们将资金投入电动汽车项目、促进农作物可持续性发展的技术开发项目,以及帮助从回收到航运等各个领域提高能源效率的软件开发项目中。
或许风险投资人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的融资风格似乎并不适合清洁技术等资本密集型领域。这个怀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同时也被夸大了。的确,清洁技术的高研发成本让风险投资公司承担了额外的风险,而需要多年开发时间的产品会降低风险投资公司的年化回报。一项研究结果显示,1991年至2019年,风险投资公司在清洁技术上的年投资回报率仅为微不足道的2%,与之相对的,软件领域的年投资回报率为24%。但据此断定绿色项目“没办法被风险投资支持”过于武断。首先,有些项目既不需要大量资金,也不需要长期投资,例如能决定家用电器何时从电网中汲取电力的软件。其次,2010年前清洁技术领域的失败,既是政府的失败,也是风险投资的失败。政客们屡屡提起要处罚或监管二氧化碳的排放,风险投资人基于这些信号采取了行动,而当政客们未能兑现承诺时,风险投资公司不出所料地蒙受了损失。2010年后,没有类似的政策冲击,清洁技术投资的表现反而更好。在2014年至2018年,绿色风险投资基金的年投资回报率略高于21%,而智能电网和能源储蓄初创企业的年投资回报率约为30%。最后,风险投资人无法管理一定数量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本书中的早期故事展示了过去风险投资人是如何在昂贵的硬件项目中获得成功的,例如仙童半导体、英特尔、天腾电脑、3Com、思科和悠游网络。
在这个行业的前几十年里,风险投资人通过撰写恰当的投资协议来资助资本密集型项目。作为他们的耐心和充足现金的回报,他们要求在被投公司中占有很大的股权份额。在20世纪60年代,戴维斯-洛克公司曾希望拥有其投资的初创企业45%的股份。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A轮融资的投资人通常期望获得所投资企业的约1/3的股权。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末,风险投资公司所获得的股权份额进一步下跌: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向谷歌注入了一大笔资金,但只收购了该公司1/4的股份。最后,在低谷时期,阿克塞尔在2005年支持扎克伯格时只得到了Facebook公司1/8的股份。若在阿瑟·洛克的辉煌时期,他甚至会觉得这份额少得可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风险投资人所获股权份额逐渐减少的趋势主要源于年轻初创企业创始人日益增长的自信。但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像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软件初创企业只需要融到有限的资金,就可以向投资人承诺快速的、天文数字般的回报。难怪风险投资人会满足于只拥有它们的少量份额。如今,如果风险投资人要为资本密集型项目融资,他们需要回顾一下过去。如果初创企业允许他们拥有大部分股份,他们未尝不可提供大量资本。
过去25年来,互联网、智能手机和云计算的迅猛发展创造了一个传说,即风险投资行业只与软件公司有关。由于许多由风险投资行业支持产生的公司都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公众眼中极具存在感,以至于不起眼的技术变得不可见,所以这个传说变得更加可信。但风险投资行业“只能”支持软件公司的说法是大错特错的。要知道,软件公司几乎涉及每一个行业,即使只支持软件公司的说法是准确的,它也很难证明风险投资仅限于一个狭窄的领域。更重要的一点是,与普遍看法相反,风险投资行业在前互联网时代投资资本密集型项目的传统如今仍然可行。
2007年,一家名为“拉克斯资本”(Lux Capital)的风险投资合伙企业募集了其首只基金,并明确要求在投资时避开那些热门行业。其联合创始人乔什·沃尔夫(Josh Wolfe)解释说:“我们不投互联网、社交媒体、手机、电子游戏这些其他每个人都在投资的领域。”相反,拉克斯在医疗机器人、卫星和核废料处理等领域进行了投资,结果证明,这些资本密集型的挑战并非风险投资行业所无法企及的。截至2020年,拉克斯资本拥有强劲的回报,管理着价值25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在2021年上半年,拉克斯资本成功从9家被投公司退出,其合伙企业又筹集了15亿美元。
旗舰创投(Flagship Pioneering)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如何获得风险投资行业支持的另一个例子。那是一家总部位于波士顿的风险投资公司,专注于投资雄心勃勃的医学突破领域。旗舰创投证明了如果风险投资公司拥有足够的优势,高风险高成本的“登月式”冒险也可以获得回报。与凯鹏华盈对基因泰克的做法一样,旗舰创投在内部孵化初创企业,在向其他公司寻求资金之前消除白热化风险。因此,当旗舰创投的项目成功上市时,它通常能保留大约一半的股权,使得该公司的有限合伙人获得极高的利润。旗舰创投孵化的创业公司,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Moderna)发明了一种针对新冠病毒疫苗。几乎没有比这更能证明风险投资效用的例子了。
当然,风险投资行业也有疏忽、遗留的错误,但没有金融专业人士能解决所有问题。涉及基础科学领域时,政府支持的实验室所提供的帮助总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估值超过5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股票市场可能会提供更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举个极端的例子,当谈到高度资本密集型的投资时,投资一家最先进的半导体工厂,财力雄厚的风险投资公司更合适。更引人注目的是,风险投资所投资的阶段范围极其广泛,包括种子投资和成长型投资,它是估值从数百万美元到数十亿美元不等的雄心勃勃的创新型初创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只要初创企业瞄准的是利润丰厚的市场,并有机会向投资人提供10倍以上的收益,其所处的行业真的不重要。例如,不可能食品公司可以发明新品种的汉堡肉,沃比帕克公司(Warby Parker)提出新的眼镜销售方式,服装零售公司(Stitch Fix)和服装租赁网站(Rent the Runway)提出新的时尚概念,Oculus(复眼)制造虚拟现实头盔,蜚比健康(Fitbit)制造健身追踪设备、小米提供价格实惠的智能手机,酸橙单车进行电滑板和自行车租赁服务,23andMe提供基因检测服务,Auris Health(奥瑞斯医疗)制造医疗机器人,Lyra Health(莱拉医疗)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条纹支付、方盒支付提供商户支付服务,变革银行(Revolut)、蒙佐银行(Monzo)提供消费银行服务。不可避免地,总会有批评人士不认同风险投资人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他们认为还有更好的选择。但这些批评人士主观的优先次序也可能受到质疑,而且似乎并非所有没得到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都是正直的。在投资能够盈利的产品时,风险投资行业至少尊重了数百万消费者的选择。
人们提出质疑的第二方面是:风险投资行业是否由来自少数精英大学的白人男性主导。相比第一种质疑,公众提出的这一质疑更有说服力。截至2020年2月,女性在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合伙人中所占比例是低得惊人的16%,但也高于2016年的11%。与之相对的,律师和医生中女性占比分别为38%和35%。诚然,风险投资行业正在努力改善这一情况,2019年,美国风险投资公司任命的新合伙人中有42%是女性,行业内的性别歧视出现了一些减弱的迹象。同时,几位因性骚扰而出名的风险投资人名声扫地,而男性也更有可能因为失礼的言论而被点名批评。在2020年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人员报告了关于厌女症的测试,他们发送了8万封电子邮件,向2.8万名风险投资人介绍有前途的虚构初创企业。假装由女性企业家发送的推销信,比来自男性企业家的同样的推销信收到的感兴趣回复多9%。但令人失望的是,这种充满希望的态度转变,没有对资金最终流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020年,只有6.5%的风险投资交易选择仅由女性创业者建立的初创企业,至少有一位女性创始人的初创企业得到投资的比例略高一些,为17.3%。
在种族问题上,改善的进展更为缓慢。公正地说,风险投资行业对亚裔投资人是开放的。数据表明,约15%的风险投资合伙人是亚裔,是其占美国劳动人口总数比例的两倍多。然而,消极的一面是,尽管美国黑人占美国劳动人口总数的13%,但只有3%的风险投资合伙人是黑人,而且黑人企业家筹集到的风险投资资金不到总额的1%。风险投资行业中这种黑人的低比例现象与其他精英职业的情况相似,但更糟糕的是:根据一个可信的基准数据,财务经理中的黑人比例为8.5%,几乎是风险投资人中黑人比例的3倍。(67)同时,拉丁美洲裔美国人的比例甚至更少。他们只占风险投资合伙人的4%,然而他们在美国劳动人口总数中占17%,在财务经理中占11.4%。这不仅不公平,而且限制了经济发展。有才华的人被剥夺了为创新做出贡献的机会。据估计,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美国的GDP将比现在高出2%以上。
2020年,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设立了一个项目,培训和资助少数具有非典型背景的创始人。这对搭档坚定地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执法面前却不平等,这很残酷。”优步的种子投资人之一首轮资本(First Round Capital)宣布,其下一个合伙人会是黑人。谷歌风险投资公司宣布任命曾在Twitter工作的黑人特里·伯恩斯(Terri Burns)为合伙人。但这些举措不过是一个开始,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该行业会被指控在不够多元化方面有罪。这里完全是毕业于少数精英大学的白人男性的天下:在拥有MBA学位的风险投资人中,有1/3的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或哈佛大学。在某种程度上,风险投资行业由精英统治。这也是批评者所称的“镜像政治”(68)。
人们提出质疑的第三方面是:风险投资鼓励失控的颠覆者。这类批评往往针对的是优步等公司的“闪电式扩张”。“闪电式扩张”这个词是由里德·霍夫曼创造的,他是格雷洛克的风险投资人,也曾是领英的创始人。这个词最初指的是被迫而不是主动选择的行为:在网络行业,赢家通吃的逻辑迫使初创企业要比竞争对手更快达到一定规模。但在轻率的投资人手中,“闪电式扩张”的意思无非是“快速致富”,这个词常与其他声名狼藉的口号放在一起,如孙正义的口号“更疯狂、更快、更大”,或马克·扎克伯格所呼吁的“快速行动,打破局面”。就连那些获得了大规模战备资金的被投公司也开始叫停这种行为了。2019年,企业家贾森·弗里德(Jason Fried)宣称,风险投资“杀死的企业比帮助的企业更多”,因为在管理者知道如何明智地花钱之前,庞大的风险投资资金会带来支出压力。“当你播下一粒种子时,它的确需要水,但如果你把整桶水倒上去,就会淹死它。”弗里德直言不讳地说。企业家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注意到许多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都失败了,他提出了一个颇具挑衅意味的观点:“闪电式扩张并不是真正的成功秘诀,而是伪装成策略的生存偏差。”
然而,奥莱利的批评与其说是对风险投资行业的控诉,不如说是对创始人的警告。如果创业的目标是自己当家做主,创业者必须明白接受风险投资是有条件的。如果创业者想要以适度的速度发展他们的公司,风险投资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然而,尽管缺乏经验的创业者可能需要被告知这些事实,但风险投资人对这些事实太了解了:他们是第一批宣称谨慎的创业者应该到其他地方融资的人。2019年1月,比尔·格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绝大多数创业者都不应该接受风险投资。”首轮资本的乔希·科佩尔曼表示赞同:“我是卖航空燃油的,但有些人其实并不想造飞机。”正如这些言论所表明的,风险投资也许有能力支持各个领域的公司,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风险投资只适合少数雄心勃勃、想要冒险、快速成长的人,而风险投资人尤其明白这一点。因为如果他们强行向不合适的公司注入资金,他们将失去投入的资金。
然而,从某种微妙的角度来看,奥莱利的批评确实揭示了一个关于风险投资的棘手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关于那些试图快速成长然后失败的创始人,因为他们自愿接受风险投资,想必知道其中的风险。相反,这个问题事关那些快速成长并取得成功的创始人,因为这些创始人会改变现有公司员工的生活。当然,为了技术进步,混乱通常是合理的代价;更重要的是,这种代价所带来的“破坏”是创造性的。但是,如果混乱不是源于技术,而是源于技术金融,那么评价可能会有所不同。当风险投资人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闪电式扩张时,就会出现一大批能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的独角兽公司,它们颠覆现有公司并不一定是因为拥有技术上的优势,而是因为得到了风险投资的补贴。例如,在网约车领域,风险投资人们人为地为乘客提供廉价车费,迫使现有的出租车运营商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中竞争。如果市场是公平的,那么即使竞争非常激烈,这在道德和法律上也都是合理的;但如果市场被操纵了,那么它就失去了合法性。
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系能够完全不存在扭曲,因此问题在于闪电式扩张造成的扭曲是否会达到有害的程度。如果有证据表明得到补贴的独角兽公司正在挤掉更有效率的既有公司,那么闪电式扩张可能会损害整体经济效率。在2018年闪电式扩张狂热的最高潮,两位学者试图做出这样的断言,他们写道:“亏损的公司可以比以往更长久地继续运营,并与现有公司进行竞争。可以说,这些公司正在破坏经济价值。”事实上,虽然这个论点在某些时候和某些行业可能是正确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几乎可以确定是错误的。
该论点之所以错误的一个理由在于市场竞争的本质。再重复一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系能完全避免扭曲,因为现有企业通常具有强大的优势。它们享有规模化经济效应和强大的品牌效应,它们参与政府法规的制定,并与分销商和供应商建立了关系。考虑到现有公司的这些优势,帮助初创企业进行闪电式扩张可能是一种平衡,而不是一种扭曲。例如,在网约车领域,现有的出租车运营商与市政监管机构关系良好,而廉价的风险投资资金平衡了这种本不公平的形势。“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优步、来福车和爱彼迎没有迅速扩大规模,它们就会被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所束缚,它们试图打造的未来不只是会出现得更缓慢,而是永远不会发生。”奥莱利评论道。从理论上讲,风险投资的巨额资金可能代表着一种过度调整。当像孙正义这样的投机者在设定步调时,反对闪电式扩张的批评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投机者式的快速扩张并不是风险投资通常会犯的错误。回想一下,比尔·格利曾对优步烧钱的速度感到恐惧;在经历WeWork的耻辱失败之后,就连孙正义也声称自己受到了惩罚。
关于闪电式扩张还有最后一点值得注意,即闪电式扩张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力量,使公司更加接近垄断地位。这可能会以三种方式危害社会:实力强大的公司可能会给供应商和工人支付过低的酬金,向消费者收取过高的费用,并扼杀创新。针对这些问题,正确的解决方式是在垄断出现时对其进行监管,而不是惩罚风险投资。毕竟,风险投资就是要颠覆根深蒂固的企业权力,它是垄断企业的敌人。例如,亚马逊面临的挑战来自风险投资支持的年轻公司,像光彩美妆等新兴消费品牌在条纹支付等新兴公司的帮助下也能够自己收取用户的账款。同样,Facebook面对的挑战来自下一代社交媒体平台,例如红杉资本支持的TikTok(海外版抖音)或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投资的Clubhouse。尽管Facebook吞并了Instagram和WhatsApp这两家过去的主要竞争对手,但Facebook面对的挑战依然存在。一方面,竞争监管机构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怀疑态度日益增长,他们可能会阻止Facebook收购未来的挑战者。另一方面,Facebook为Instagram和WhatsApp支付的高价,为风险投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让他们为下一轮的竞争者提供资金。
任何像沙丘路的居民一样变得富有和强大的小集团都应该受到严格的审查。但在上文提到的三种质疑中,只有一种是有价值的。风险投资行业确实是一个小圈子:白人太多,男性太多,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太多。一个对未来格局影响如此之大的行业应该更加认真地对待多样性。但说风险投资不适合清洁技术等对社会有用的行业,这是不对的。“要么做大,要么回家”的闪电式扩张心态通常也不会极端到损害经济效率的程度。随着技术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垄断的出现到假新闻的传播,再到对隐私的损害,民众有理由担心它的弊端,但这些威胁来自成熟的科技巨头。风险投资非但不会巩固这些平台,反而很可能颠覆它们。
与此同时,为了对风险投资人作一个整体的评估,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的优点。商学院和金融学教授们已得出结论,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对财富创造和创新具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在美国,只有1%的公司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但乔希·勒纳(Josh Lerner)和拉玛纳·南达(Ramana Nanda)在一项涵盖1995年至2019年这25年的研究中发现,风险投资支持的能够进行IPO的公司数量占美国非金融类企业总数的47%;换句话说,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比没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更有可能上市。此外,由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往往比没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同行做得更好,产生的创新也多得多。因此,尽管风险投资支持的能够上市的公司数量占非金融类企业总数的47%,但在研究结束时,它们占非金融类上市企业市值的76%,它们的研发支出也占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整体研发支出的89%。另一项研究证实,更多的风险投资会激发更多的专利申请,而且风险投资支持企业的专利的重要性高于平均水平:在风险投资支持企业的专利中,有22%的专利都位列被引用数最多的专利的前10%。这些知识成就为经济中的其他部分带来了生产率溢出效应。一家公司创造的技术可能对其他公司有用,而他们创造的创新产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高个人和企业的效率。
风险投资支持的一些公司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但通常有一个问题:是风险投资创造了成功,还是他们只是出现在有成功公司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另一项研究表明,具有风险投资指导优势的初创企业比同行表现得更好,本书也涉及了多个风险投资对被投公司产生积极影响的相关案例。此外,即使风险投资的技能完全在于挑选交易,而不是指导初创企业,这种技能仍然是有价值的。明智的交易选择增加了最值得投资的初创企业获得所需资金的机会,它确保社会储蓄得到有效分配。
此外,我们在分析这种以金融为中心的风险投资案例时也应该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多亏了安娜莉·萨克斯尼安的研究,人们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认识到,硅谷之所以能取代波士顿成为创新中心,是因为它的人际网络质量:相比马萨诸塞州封闭的企业,人才和思想在加州的小型初创企业中能够更自由地流动。本书进一步推进了此观点:萨克斯尼安所强调的丰饶网络首先是由风险投资人培育出来的。在启动加利福尼亚州的创新飞轮的过程中,阿瑟·洛克的重要性不亚于斯坦福大学的存在或大量的国防资金的投入。在赶超波士顿的过程中,硅谷依靠的是风险投资团队。就像3Com公司的故事所说明的一样,这家以太网公司曾寻求东海岸的融资,但最终它意识到西海岸的风险投资是不可替代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崛起也可以追溯到风险投资的影响。与硅谷自身的发展类似,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起步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或在美国接受了培训的风险投资人的帮助。风险投资对应用科学商业化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贡献在不断发展,并将继续增加。从1980年到2000年,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在美国IPO企业中所占比例已经很高,达到35%。在随后的20年里,这一比例跃升至49%。由于经济的根本性转变,未来风险投资将进一步发展。在过去,大多数企业投资都是有形的:资金用于购买实体商品、机器、建筑、工具等。但如今很多公司的投资是无形的:资金用于研发、设计、市场研究、业务流程和软件。现在对无形资产的投资正好是风险投资最擅长的:早在1962年解释风险投资时,洛克就说他所投资的是“知识账面价值”。相比之下,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对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构成了挑战。一般情况下,银行和债券投资人试图通过担保“抵押品”来保护自己免受损失,这些“抵押品”通常是借款人的资产,可以在借款人违约时被没收和出售。但是无形资产显示了其沉没性:一旦投资完成,金融机构就没有实物可以通过拍卖来收回资本。同样,传统的股权投资人在评估公司时,部分依据的是财务报表中清楚显示的实物资产的合计价值。但无形资产更难衡量,它们避开了标准的会计准则,而且它们的价值是不透明的:例如,要评估一个软件开发项目,你必须了解这个技术。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有形资产正在被无形资产所取代,只有亲力亲为的风险投资人才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本。
因为风险投资特别适合为无形资产融资,所以它在地理上的扩展也就不足为奇了。硅谷仍然是这个行业的中心:在美国境内,2/3的美国风险投资合伙人住在硅谷,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风险投资募资中的份额从2004年的44%跃升至2019年的62%。然而,与此同时,这里的投资人越来越愿意支持位于其他州的公司。风险投资行业内的资金呈爆炸式增长,使得大量资金流向硅谷之外的风险投资合伙企业。最大的受益者是传统金融中心波士顿和纽约,但资金也流向了强大的工业城市,如洛杉矶和西雅图,甚至流向了更令人惊讶的地方,例如,由两名红杉资本前员工领导的驱动资本(Drive Capital),在俄亥俄州的总部管理着价值1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随着2020至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远程工作的出现,一大批技术精英放弃了交通拥堵的硅谷,寻找税收和租金更低的地方,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和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成为两个热门目的地。一家名为8VC的风险投资合伙企业的负责人乔·朗斯代尔(Joe Lonsdale)认为,他搬到奥斯丁也是押注创新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他写道:“有才华的人正在全国各地建立顶尖的技术公司,我们打赌美国的未来将建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在这个有良好的政府管理和合理的生活成本的地方。”
风险投资中心在美国以外地区的发展,凸显了风险投资在为未来产业融资方面的优势。从2009年到2018年,风险投资排名前10的城市中有4个来自美国以外:北京、上海、深圳和伦敦。以色列、印度和东南亚等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有前途的风险投资集群。就连通常在数字领域处在落后地位的欧洲,在2015年至2019年的5年里,风险投资公司数量也翻了一番。2021年,有3名拉丁美洲人登上了《福布斯》的最佳创投者名单,这是该地区首次有人上榜。总的来说,美国在全球风险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2006年至2007年的约80%下降到2016年至2019年的不到50%。上一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认为美国是唯一适合开办公司的地方,但如今,他们发现机会无处不在。
全球对风险投资的广泛接纳证实了我们之前的论点:该行业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其所谓的缺点。作为个人,风险投资人确实展现出其技能;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资助最具活力的公司,创造不成比例的财富和研发成果,并将推动知识经济的丰富网络连接在一起。未来,随着无形资产逐渐超越有形资产,风险投资人亲力亲为的风格将为社会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有许多社会问题风险投资行业无法解决,有时还可能火上浇油,例如不平等问题。但对不平等问题的正确回应是,不要怀疑风险投资的重要性,或者在它的齿轮上撒沙子。解决方法应该是向那些在上一代人中暴富的幸运儿征税,包括那些作为风险投资人发家致富的人。
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支持,往往会引发两极分化的争论。一方面,技术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干预对激发创新没有任何帮助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互联网起源于五角大楼的国防项目,而马克·安德森是在政府支持的大学实验室工作时制造了第一个网络浏览器。1980年前后,美国政府的两项政策改变——取消养老基金注资风险投资的限制,以及降低资本利得税,有力地推动了资金流入美国风险基金。另一方面,相信政府产业政策的人也同样错误地掩盖了政府干预的反复失败。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对SBIC的支持基本上是一种浪费;事实证明,SBIC远不如私人有限合伙企业高效。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纳税补贴与该行业的复苏关系不大;私营企业从芯片制造向创新芯片设计的转变更为显著。同样,在中国,国家对科学教育和研究的投资也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发展。
其他国家的案例则明确显示,政府行为并不天生就具有好或坏的影响,效果取决于设计细节。1993年,以色列领导人发起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风险干预之一:用一只名为尤兹玛集团(Yozma Group)的1亿美元的政府基金补贴愿意在以色列设立公司的外国风险投资:如果私人投资人向一只基金投入大约1200万美元,尤兹玛集团将以慷慨的条款再投入800万美元,共同承担前期投资风险,并限制尤兹玛集团对未来利润的要求。这只优惠基金与监管措施相结合:外国投资人被允许使用有限合伙企业结构,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并尽量避税。通过“聚集”技术娴熟的风险投资人,以色列将其丰富的科学人才储备变成了蓬勃发展的初创企业集群。在尤兹玛集团成立前,以色列只有一只活跃的风险投资基金。10年后,以色列政府停止了对该行业的补贴,60家私人集团管理着约100亿美元的资产。到2007年,以色列的风险资本在GDP中的占比高于其他所有国家。
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看欧盟的风险投资干预措施。2001年,欧盟委员会拨款超过20亿欧元用于风险投资补贴。但它未能将这笔资金与支撑以色列成功的设计特色结合起来。欧洲不承认有限合伙企业合法,没有解决累赘的劳动力市场监管,也未能建立有利于初创企业的股票市场以促进风险投资的退出。结果,欧盟的干预措施并没有让风险投资人蜂拥而至,而是把他们排挤出去了:由于欧洲的创业机会有限,风险投资合伙企业没有兴趣与政府资助的投资人竞争。更糟糕的是,由于政府资助的投资人比私人投资人缺乏技能和积极性,这种替代降低了欧洲风险投资的质量:交易选择和投后指导情况恶化。从风险投资行业建立之初到2007年底,欧洲风险基金的平均回报率为-4%。
综上所述,这些错综复杂的政策实验为促进风险投资提供了一个警示和四个教训。警示是,以色列是不同寻常的;新加坡和新西兰是少数几个成功效仿它的国家。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将纳税人的钱注入风险投资基金被证明是无效的。
理论上,通过补贴资本成本来促进创业的想法是合理的:这样政府在帮助创业者的同时,会认识到风险投资人更擅长选择初创企业,更重要的是,风险投资人也更擅长从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撤资。但受政府补贴的风险投资企业有时也会呈现出政府的某些特质:官僚主义、不奏效的激励机制、任人唯亲。2009年,哈佛商学院的乔希·勒纳发表了一篇权威专著,阐述政府为推动风险投资付出的努力,他称之为“碎梦大道”。
鼓舞人心的一面是,关于促进风险投资的第一个经验教训是,减税比补贴更有效。政府为风险投资人提供资金补贴行为可能会使风险投资人的决策变得草率,因为投资失败的一部分损失将由纳税人与之共同承担。而税收优惠既能降低投资于初创企业的资金成本,也会创造更健康的激励机制。投资人必须为最初投资的每一美元自掏腰包,他们有理由深思熟虑后再选择是否承担风险。与此同时,减税确保了如果投资顺利进行,风险投资人将保留更多的上行空间。这加强了对风险投资的激励,促使他们做出最明智的投资,并为投资组合公司付出额外的努力。
美国最成功的风险投资税收减免机制体现在有限合伙企业上。除其他优点外,这种结构避免了公司被征收双重税负。美国政府对普通公司的利润,通常首先在公司层面征税,然后在公司将利润作为股息支付给股东后,在股东层面征税。相比之下,有限合伙企业被归类为“传递实体”:他们将成功投资的收益免税传递下去;合伙人在收到分配的利润后只需缴纳一次税款。自戴维斯-洛克时代以来,有限合伙企业一直主导着美国的风险投资行业,而其他一些国家随后也接受了这种结构。然而,一些国家仍然不允许设立传递式的合伙企业,因为他们不希望富有的投资人逃税。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是不理性的,政府可以想办法让富人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而不损害创业激励。例如,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可以与更高的遗产税相结合。
第二个政策经验是,对风险投资人的税收减免应该与对初创企业员工的激励相结合。为初创企业工作可能是残酷的:一项研究发现,几乎75%的由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在关闭时根本没有挣到任何钱。将精力投入这些企业的人才还有其他选择:他们可以在大公司任职挣得高薪。为了吸引人才远离舒适的安全区,奖励必须很丰厚,而且社会也应该希望如此,因为充满活力的初创企业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因此,政府应该支持员工获得股票期权激励,这已成为现金匮乏的初创企业吸引世界级干将的最佳手段。然而,尽管英国、加拿大、中国、以色列和波罗的海国家等已经采纳了保障员工期权可行的法律和税收规则,但其他国家却拒绝这样做。在一些欧洲国家,法律不承认不带投票权的股票授予;因此,要使用期权,初创企业就会变成治理噩梦。在其他地方,股票期权在授予时征税。例如,比利时对获得期权的员工征收18%的税,即使期权最终可能毫无价值。2020年,法国为让员工期权可行而修订了法规,德国财政部长承诺会跟进。但该地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初创企业的员工拥有的公司股票数量是他们欧洲同行的两倍。
除了提供低成本的资本和员工股票期权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激励发明来鼓励科技初创企业。第三个政策经验是,政府必须投资于科学——包括培养年轻科学家以及支持与商业化相去甚远而无法吸引风险投资资金的基础研究。对大学实验室的投资必须与允许将由此产生的成果商业化的法律规定相结合。在美国,1980年的《贝多法案》(Bayh-Dole Act)允许大学为在联邦政府研究拨款的资助下产生的发明申请专利,并将这些专利授权给初创企业使用。因此,许多美国大学建立了先进技术转让办公室,将发明家与风险投资人联系起来。正如产业集群依赖于资本和人员的快速循环一样,知识产权必须被释放以寻求其最有效的用途。
最后一项政策经验是,政府应该放眼全球。他们必须通过大方地发放签证来吸引外国科学家和企业家。接受国际公认的税收规定和国外风险投资人满意的法律形式。如果国内股票市场不发达,他们应该鼓励年轻公司在国外市场上市,不应该以牺牲开放的全球竞争为代价来为本国公司提供特权。一个国家与其他经济体的联系越多,风险投资人寻找初创企业的动力就越大:更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会带来更大的投资机会。以色列蓬勃发展的部分原因是其初创企业从一开始就旨在制造其他国家的人会购买的东西。讯佳普和声田等非常成功的企业就是通过从国外风险投资公司那里获取资金并面向国外消费者而做大做强的。
综上所述,在大多数情况下,四个简单的步骤将带来更多回报:鼓励成立有限合伙企业,鼓励初创企业员工获得股票期权,投资于科学教育和研究,同时,放眼全球。
本书充分论证了风险投资充满活力的秘诀:如果其他人被一个问题吓倒了,那么机会就在那里。宁可尝试后失败,也不要不敢去尝试。最重要的是,请记住指数法则的逻辑:成功的回报将远远大于失败的代价。这一令人振奋的法则已将风险投资变成了国家力量经久不衰的支柱。

 上一篇
上一篇